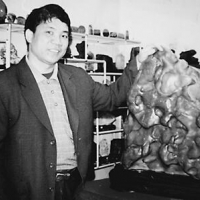胡篆刻“玉芝堂”

胡篆刻“晚翠亭長”
胡(1840-1910),字匊鄰,號廢鞠、不枯、晚翠亭長。浙江石門(今桐鄉)人。自幼隨父宦游,遍覽江山名勝與前賢手跡。及長從費丹旭之子費以耕習畫,所繪山水近髡殘,仕女、花卉均秀逸有致。胡游藝于上海及蘇杭兩地期間,與書畫家、收藏家金鑒、楊晉、高時顯、葛昌楹、吳滔、吳徵、丁仁、吳隱廣結金石之緣,為他們鐫刻了數量不菲的印章。篆刻名家徐三庚年長胡十四歲,與其相知相惜,為其精心刻制了“匊粼日利”、“胡”二印。同年(1865)兩人又合作了一方精彩的“胡印信長壽”白文印,由徐氏篆稿,胡走刀。事實上兩者的合作尚多,這在五百年印史上堪稱是一個孤例。此外吳昌碩也與胡相遇于湖州,欣然定交,皆傳為印林佳話。
胡還精于刻竹、刻木、雕硯與鐫碑。位于西泠橋畔的秋瑾墓碑,就是由吳芝瑛書丹,胡刻碑。胡篆刻專宗秦漢,“宋元以下各派絕不擾其胸次”。所作朱文別于時人的玉筯鐵線,作粗闊的處理,白文則作細于漢玉印清朗明凈的處理,并借鑒秦詔版與漢魏鑿印中的穿插、避讓、欹側等手法,輔以瘦勁挺拔的刀法,使印作在渾樸妍雅、疏密自然中表現出一種有意無意的錯落之美。胡尊奉秦漢的傳統審美觀,得到了晚清至民國初期同樣有古典情結的一批文士與藝術家的賞識,推崇他稱:“印之正宗,當推匊鄰”。胡表現出一種貌似漫不經心的大智若愚、大巧若拙的智慧與趣韻,確實需要細細品味的。
然而站在近代篆刻藝術發展歷史的高度來觀察,胡雖不受流派印風的染惑,表現出了自覺的藝術追求個性,但他未能擺脫“印內求印”的傳統束縛,也沒有形成一套獨特的篆書風格,刀法和篆法游離于浙派與六朝朱文之間。胡白文印造詣極深,不凡精彩之作,但其藝術語言的表現力還是相對單一、薄弱,成功作品的數量與晚清四大家中其他三家相較,也處于明顯的弱勢,加上其弟子甚罕,藝術也未曾得到很好的揄揚,當進入流派紛呈、標新立異的民國時代時,其感染力和影響力的消退是必然的。
胡朱粗白細的風格在彼時的印壇是清新的、鮮明的,但畢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有高度、深度的創新,尤其是在古往今來、濯古出新的熠熠印史里會顯得相對黯淡,也許這正是他不足與趙之謙、吳昌碩等大家相比肩的理由。
珍稀奇打造企業家收藏交流學習的綜合信息平臺——企業家收藏網
注:本文部分內容圖片來源于網絡,僅代表原作者觀點,如有版權問題,請及時告知刪除!